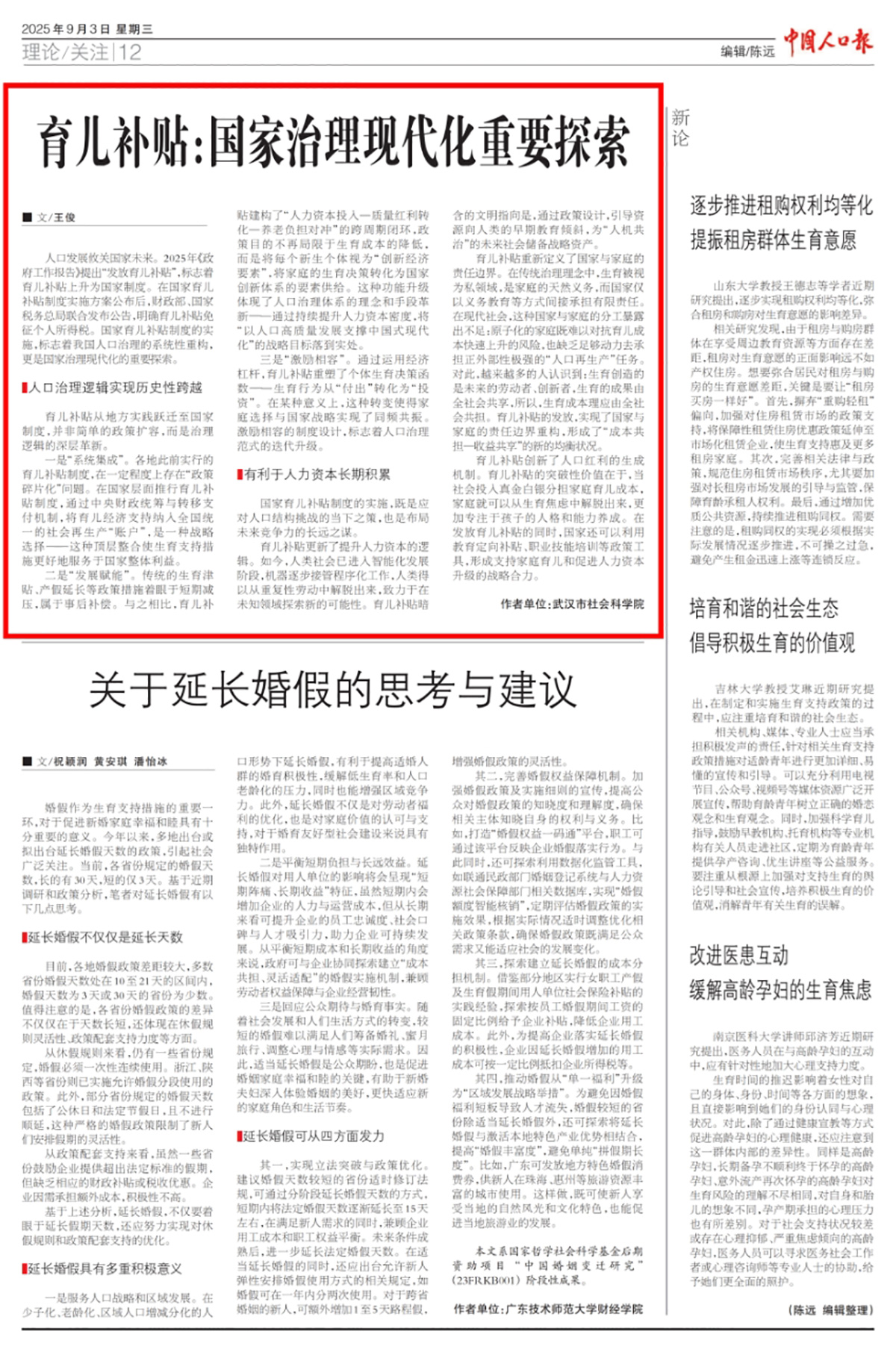□ 王俊:博士,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
人口发展攸关国家未来。2025年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提出“发放育儿补贴”,标志着育儿补贴上升为国家制度。在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公布后,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前不久联合发布公告,明确育儿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。国家育儿补贴制度的实施,标志着我国人口治理的系统性重构,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探索。
从民生政策到国家战略的历史性跨越
国家层面推行育儿补贴制度,这一跃迁并非简单的政策扩容,而是治理逻辑的深层革新。
从“政策碎片”到“系统集成”。以地方为单位实施的生育补贴制度,很容易陷入“补贴竞赛”或“断供困境”:经济强省以高补贴吸引育龄期人口流入,打造生育高地,而财政弱省则难免落入生育洼地。在国家层面推行育儿补贴制度,通过中央财政统筹与转移支付机制,将育儿成本纳入全国统一的社会再生产账户,这是一种“以空间换时间”的战略选择——牺牲地方竞争所产生的短期效率,换取人口结构的长期均衡。这种顶层整合,消解了地方博弈的负外部性,使人口政策真正服务于国家整体利益。
从“应激补偿”到“发展赋能”。传统的生育津贴、产假延长等政策措施着眼于短期减压,属于事后补偿,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则建构了“人力资本投入-质量红利转化-养老负担对冲”的跨周期闭环,政策目的不再局限于生育成本的降低,而是将每个新生个体视为“创新经济要素”,将家庭的生育决策转化为国家创新体系的要素供给。这种功能升级回应了人口治理的根本矛盾——少子化情境下,唯有持续提升人力资本密度,才能实现“以质量替代数量”,将“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”的战略目标落到实处。
从“行政管控”到“激励相容”。通过经济杠杆,育儿补贴制度将重塑个体生育决策函数——当补贴额度超过家庭育儿的机会成本,生育行为便从“负担”转化为“投资”,某种意义上,家庭选择与国家战略便实现了同频共振。这种激励相容的制度设计,标志着人口治理向“赋能家庭”范式的迭代,同时也避免了管控性政策可能产生的反弹风险。
重构生育文明的中国治理答卷
国家育儿补贴制度的实施,既是应对人口结构挑战的当下之策,也是布局未来竞争力的长远之谋,它开启了一场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大思考。
将育儿补贴上升至国家层面,改写了基于工业文明的生育逻辑。进入智能化发展阶段,机器逐步接管程序化工作,人类得以从重复性劳动中解脱出来,致力于在未知领域探索新的可能性。育儿补贴制度暗含的文明指向是,通过政策设计,引导资源向人类的早期教育倾斜,为“人机共治”的未来社会储备战略资产。这改写了工业文明“以数量取胜”的生育逻辑,在实践层面构建起数字文明的人口伦理新范式。
育儿补贴制度重新定义了国家与家庭的责任边界。传统治理中,生育被视为私领域的事情,是家庭的天然义务,而国家仅以义务教育等方式间接承担有限责任,家庭负责“生产人”,国家则负责“管理人”。少子化情境下,这种分工暴露出严重缺陷:离子化的家庭既无力对抗育儿成本飙升等系统性风险,也缺乏足够动力去承担正外部性极强的人口再生产任务。育儿补贴制度不是简单的福利供给,它所建构的,是现代社会的新型契约关系。在这种新型关系下,生育创造的是未来的劳动者、创新者和纳税人,生育的成果由全社会共享,所以,它产生的成本也理应由全社会共担。这种责任重构,意在打破“国家-家庭”的零和博弈困局,形成“风险共担-收益共享”的新的均衡状况。
育儿补贴制度创新了人口红利的生成机制。传统人口红利建立在大量低成本劳动力的基础上,其本质是通过压缩个体发展空间,换取集体增长。这种增长模式在新时代陷入双重困境:一方面,创新经济需要的是质量更高而非数量更多的人力资本投入,而另一方面,家庭却因育儿成本高企,被迫降低对孩子质量的投资。育儿补贴制度的突破性在于,它以公共资源注入重构了“数量与质量”的博弈方程——当社会投入真金白银分担家庭养育成本,家庭就可以从生育焦虑中解脱出来,更加专注于孩子的人格和能力养成,而国家则可以通过教育定向补贴、技能培训、税收抵扣等政策工具,将分散的家庭选择转化为人力资本升级的战略合力。这重构了新发展阶段人口红利的生成机制。
育儿补贴制度重塑了文明延续的价值基石。工业文明将生育异化为经济计算,生或不生被认为取决于“成本-效用”的简单对比。这种工具理性消解了文明延续的精神内核。国家育儿补贴制度的建立,重构了生育的意义坐标系。未来,生育可以不再基于经济考量,生养孩子不仅仅是为了承担责任、履行义务,更不仅仅是为了养老,它可以单纯是因为“爱”、因为人性,甚至因为对生命本身的敬畏与期待。在算法统治、物质至上的时代,生育是人类对抗异化的堡垒,它证明文明存续的根基不是算力的堆砌或数据的积累,而是人性的温度与代际的共情。生育的本质不是对劳动力的制造,而是对未来的信仰。